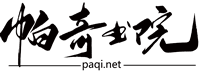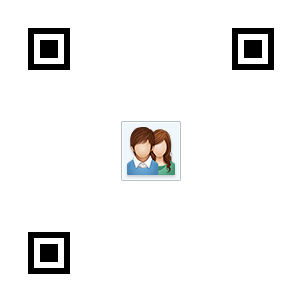张晨以为自己睡了很久,醒来的时候看看手表,才四点钟,感觉到嘴里有点干,他起身去倒了一杯水,端着杯子走到窗前,拉开窗帘,看看外面,天还是黑沉沉的,远处海天之间,混沌一片,下面酒店的花园里,却是一片的繁星闪耀。
张晨走回到床前,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,重新倒在了床上,却已经没有睡意,他干脆又坐起来,打开门走出房间,去楼下,他想再画几笔。
电梯门打开,酒店还没有开始营业,下面的大堂,光线昏暗,一个人也没有,总台那里空空荡荡的,值班的保安,在靠近大门口的一张沙发上,垂着头睡着了,张晨往右边踅过去,去往大堂吧的方向,他们的画室就放在那里。
刚转过去,张晨就愣住了,他看到画室那里,开着灯,姚芬一个人还在画画,张晨走过去,快走近的时候,轻轻咳了一声,姚芬听到声音,转过身来,看着张晨笑了一下,人却是有些局促的。
张晨问道:“这么迟了,怎么还不去睡?”
“睡不着,就到下面来画画了。”姚芬说,“你怎么也没睡,老板?”
张晨笑道:“我是已经睡了一觉,不想睡了,想来画画。”
两个人都笑了起来,这一笑,姚芬才觉得放松了下来。
张晨走过去,走到了自己的那幅画前面,打开油画箱,用刮刀把调色板上面的颜料刮干净,这是张晨的习惯,他总是喜欢在重新开画之前,清理调色板,就在清理调色板的时候,人慢慢会情绪稳定下来,开始进入状态。
开始画画,两个人就进入了比较随意和舒适的状态,一边画画,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也可以保持沉默,就是说话,语言也都是很简洁的。
张晨问:“现在好吗。”
姚芬嗯了一声。
两个人手里的笔,并没有停下来,过了几分钟,张晨继续问:“新工作还适应吗?”
“还好。”姚芬轻声说。
两个人不再说话,自己管自己画着,张晨的出手很快,画完之后,几乎很少有再回去修改和调整的地方,继续画了十几分钟,他就快画好了,扭头看看姚芬,姚芬抿着嘴,眉头微蹙,盯着她自己的画看。
张晨手里握着画笔,退到了姚芬的身后,双手抱在胸前站在那里,看着姚芬继续画,看了一会,张晨说:
“姚芬,你现在用色,比原来狠了。”
“是吗?”姚芬说,“我自己还没有感觉,我都,我都很久没有画了。”
姚芬说着,声音里有一种淡淡的哀怨,张晨心里叹了口气。
张晨站着,又看了一会,走回去自己画前,把最后的几笔画完,用草纸把笔擦干净,一边擦一边盯着自己的画看,确认不需要再修改了,他把笔浸泡到了松节油里。
“老板,你好了?”姚芬问。
“好了。”张晨说。
姚芬走过来看看,赞叹道?就是一个大学教授在我面前,他知道的也不一定比我多。
“人真的不在于你是什么身份,多高的学历,要是学习态度不行,对世界没有好奇心,故步自封,那都是瞎掰,就是大学教授,也很快会沦落到和文盲差不多。”
“牛逼!”刘立杆叫道,“不过,我觉得张晨说的也是对的,你们女人,太注重形式,确实是这样,我就觉得,我自己在海城扫楼的时候,学到的最多,那个时候,感觉自己全身心打开了,方方面面都在学习,而且,吸收得很快。
“确实,学习的态度,比学习更重要,张晨总结得很到位,不愧是浙美的。”
张晨笑道:“哪里哪里,你浙大的也不错。”
谭淑珍和小昭说:“看这两个臭不要脸的,还互相吹捧沾沾自喜了,张晨,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,但我感觉,像你说的这样学习,是零零碎碎的,不够专业,要学专业的,还就是要老老实实,照着课本学。”
“就是。”小昭说,“就像我着自己的画看了一会,轻轻地叹了口气,和张晨说:“好吧,你是对的。”
“画画的,都以为起手很难,其实,收手更难,知道在什么时候收手,最难。”张晨说,“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也曾经陷入这样的迷失中,那就是总是收不了手,自己看着自己的画,总觉得还有遗憾,想表达得更完美,不停地去改。
“结果,越改毛病就越多,改到自己都丧气了。
“后来渐渐明白了,其实,每一幅作品,都是有遗憾的,你让达芬奇让伦勃朗或鲁本斯,看自己的作品,都是会有遗憾的,不过,他们有一个好处。”
“什么好处?”姚芬问。
“那就是,他们的画,都是别人订制的,是有交货时间限制的,你从鲁本斯的很多画里,都看得出来,最后一笔落在哪里,看得出来他是急匆匆的,为什么,生意太好,业务繁忙,每一幅画,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完成它。
“都是临要交稿了,到法国的船或者马车,马上要走,没有时间了,他必须抓紧最后的时间完成。”张晨说。
姚芬轻轻地笑着:“你看画就注意这些啊?”
“对。”张晨笑道,“我很容易陷进去,我看画的时候,很容易把自己就搞混成那个画家了,感觉自己在画着,从哪里开始,到哪里结束,中间什么地方,反复修改了,我看鲁本斯的时候,感觉自己就是鲁本斯,看毕沙罗的时候,感觉自己就是毕沙罗。
“他们的那种开心我感觉得出来,像毕沙罗,他画着雪后的巴黎街道时,他的心情是多愉快啊,不愉快就画不出来空气那么清新的天空,我都感觉得出来,他是一边吹口哨一边画着的。
“看的多了,感受的多了以后,我也明白了,没有任何一幅作品是没有遗憾的,遗憾就是作品的组成部分,明白了这点之后,我画画的速度就快了起来,也知道在哪里收手了,姚芬,你知道我为什么画画画得很快吗?”
“为什么?”姚芬问。
“我在追气。”张晨说,“中国话里,很多话是很奇妙的,比如一气呵成,气韵生动,我就是在追一气呵成的这口气,一幅作品,是有自己的节奏的,它在自己的节奏里,气韵生动,你追上这口气,一气呵成了,作品就完成了,完成的时候,也就是断气了。”
姚芬轻轻地笑了起来。
“真的,这一口气断了之后,你再去改,就很别扭了,我这个说法,不光光画画是这样,音乐更加,你去听一部交响乐,四五十分钟,从头到尾酣畅淋漓,那是一个很缜密的演绎,对吗?”
姚芬点了点头。
张晨看着姚芬说: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,作曲家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,可不是只用了四五十分钟,而是几个月,一个一个音符这么写出来,改出来的,这个过程,他可能绞尽脑汁,可能呕心沥血,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,但能够支撑他走下去的,就是那口气一直在。
“要是不在了,作曲家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,他只能把它放下,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未完成作品存在的原因。
“我们画画,其实也是这样,丼?我不开心了,幸好谭大哥给刘大哥打电话的时候,我们正好在刘大哥那里。
老唐叫道,不用叫,来抢就是。
张晨赶紧解释,他说,我不是以为老唐在厂里,你在家要带小孩走不开嘛,对了,那个小老唐呢?
“阿姨带着。”林淑婉说。
大家进去,把一个包厢都塞满了,慧娟和他们说,今天你们这桌,都是我爸爸烧,都是土菜,你们不要见外,还有,他今天第一次用我这厨房,有点不太习惯。
“越土越好。”汉高祖刘邦说,“慧娟,让你爸爸,把最土的菜拿出来。”
慧娟说好。
第一个上来的,果然就是一道很土的菜,吓了他们一跳,特别是林淑婉,阿巧端上来的是,在一只不锈钢的托盘里,坐着一整个的咸猪头,老唐一看就大叫一声,伸手一扯,猪头已经煮得稀烂,老唐把一只猪耳朵抓到了手里。
大家纷纷动手,一边吃一边叫好,老唐把那只耳朵,伸到林淑婉的靜?停车场里,一边抽烟一边聊天,看到张晨出来,两个人赶紧把手里的烟放下,藏到了手背后面,身子也站直了,张晨和他们摆摆手说,辛苦了。
张晨和姚芬,两个人走到了花园的尽头,一直朝外面的海滩走去,细细的海风吹过来,有点凉,海浪缱绻着沙滩,他们看不到远处的海浪,但能够听到它不知疲倦的哗哗的声响。
黎明前的这个时候,是天最黑的时候,离日出还有一个多小时,天上的星星又已经藏匿了起来。
两个人朝海浪响动的地方走去,也就是朝着大海走去,走到了模模糊糊,已经可以看到大海,看到海里那一层一层,不断地推进的白色的浪线时,凭经验就知道,再往前走,沙滩是潮湿的。
“我们就坐这里等吧?”张晨说。
姚芬说好。
两个人把脚上的人字拖脱下来,放在了沙滩上,然后人,并排坐在了人字拖上。